八年前,一个叫“瓦依那”的广西壮族乐队,
在自家仓库里录制了三张专辑,
随后销声匿迹,踪影难寻。
有乐评人称“那歌三部曲”是沧海遗珠。
“对这个时代来说,
这样的音乐几乎算是回光返照。”

▲
广西河池的那田农舍
消失的这些年,
主唱岜農一直待在河池老家,
守着一块叫“那田”的土地。
盖房子,种树插秧,养鸡养鸭,
像一个古代的农民,
“低头种地,抬头唱歌”。
他用自然里的一切做音乐,
树叶、葫芦、酒缸、竹子、打谷桶……
音乐人老狼说他的家是
“南中国向往的地方”,
乐评人拉家渡形容他
“站在小镇望星空,
不离不弃,精神自足得可怕。”

▲
在打谷桶和油菜花屋顶下弹吉他

▲
在喀斯特溶洞前吹壮萧,回声悠扬
去年底,瓦依那乐队重现在大众视野,
开始“种地十年”巡演。
吉他手十八是农民,
鼓手路民是泥瓦工,
演出门票只要31块3,
互动礼物是岜農种的一袋大米。
他们说要发出农民的声音。
夜色温柔,岜農弹着他的葫芦琴,
向我们讲述这些年的故事。
蛙声一片,萤火虫像星星眨着眼睛,
我们愿意相信他说的:
“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”
自述:岜 農
撰文:洪冰蟾
责编:倪楚娇


▲
岜農在水田里育苗
贝侬贝侬回家咧/回家种地咧/别去追那辆火车拥拥挤挤的火车
回家咧回家咧/在那你只能变得很弯很扁长出刺来/回家咧回家咧
--《回家种地》
我是岜農,“岜”就是广西石头山的意思。简体的“农”是一个“犁”的样子,就是干活。繁体的“農”,上面有个“曲”。古代的农民劳作之余唱歌,唱田间地头的一些歌,自己生活的喜怒哀乐都在里边。
这个状态是我喜欢的,石头山不怎么好发展,保持着自然的状态。我就躲进石头山里,生活在稻田边。生活也是艰苦的,但是唱起歌来就不会那么消沉,已经融化成一股山风,摇晃的树叶。

▲
劳作结束,坐在前廊拨弄水竹琴
我父母都是河池的农民,我从小就在田里放牛割草。后来去广州做了八九年设计,其实在办公室里坐一个小时就够我觉悟了,我还是想要自由。
十年前的春天,我回家插秧,一直到秋天收割完,又回到城里上班。就这样持续了3年后,我决定彻底回家,陪伴父母,不“跃农门”了。

▲
一栋两层田舍,水田3亩,旱地2亩,山林果园30亩
我们村隔壁,高速公路通不到的地方,有一个更深的村。那里有一幢空置的老房子,屋前有小块土地,后山上有几汪泉水。2018年,我租下这里,弄了个小小的农场,种了四五亩老品种的水稻。我把这里叫“那田”,古壮字里,上面“那”下面“田”就是水田。
我的发小邻居都惧怕做现代的农民。小孩的奶粉、结婚的房子,用劳动来换的话,太悬殊了,撑不下去的。
但一尺之隔,农又是最赚的,只是拿来吃饱的话,太容易了。撒一颗种子,发三粒的话,一个种子可以回报1000粒米,你买股票哪有这么赚?

▲
大暑,吹“喂鸭调”,稻田里的小鸭子排着队现身

▲
处暑,给第一波稻子脱粒,敲响谷鼓
我不是普遍的现象,现在的生活是半农半X。一年只种一季稻,谷雨育苗,立夏插秧,秋分收割。冬天就出门旅行去,想去哪就去哪,到春天再回家。种的米只是保证我有饭吃,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,多出来一小部分会卖。农闲时候,叫上瓦依那乐队的成员去做巡演,带小朋友上自然教育课,帮村里的小学、博物馆盖房子,用这个来挣钱。
我这个要求不高,有一碗粥,一把笛子,一个月亮,好像就够了。所以我就勇敢地选择了这条以种地养自己,让自己在很安心的情况下,去做喜欢的事情。


▲
从山上采来野花和笋,开始做饭
我唱我的家/村边有个绿荫塘/四面青山环绕/屋前李子花开
我唱我们的歌/这条没有名字的河/在这两岸的田野上/勤快的人是日出又日落
--《没有名字的河》
以前遇到一个农民朋友,他要起一个房子。隔了两年我去看他,卫生间都没有,但是已经装了一个豪华的铁门和两根罗马柱。
我在想,他花了两年时间去做很苦的活,拉马、拖木材,就是为了赚铁门和罗马柱?那些时间我可以用来摘一朵花,喝个茶,看个月亮。难道我们要住一个美丽的房子,一定要花半辈子的上班时间才能打造吗?

▲
瓦片、窗户、小物件都是收来的旧物

▲
忍冬随风飘荡
我整个房子的窗户是一个小学拆掉的旧窗子,花了50块钱,还没用完。村民拆掉平房去修罗马柱,那些老的瓦都不要了,我就捡破烂一样,东收一点西收一点。墙用这里的黄泥、石灰和稻草混合在一起,不用空调,冬暖夏凉。

▲
客厅一侧放着老种子,一侧放着乐器

▲
在火塘生火
一楼是一个有火塘的厨房,客厅和做音乐的工作区,还留了一个门口的回廊、看星星和萤火虫的草坪。

▲
二楼卧室

▲
望见窗外的田园风光
加盖的二楼,留出了两间卧室。平时就我一个人在这里,偶尔有朋友来的话就腾出来给他们。算是个不对外开放的民宿,听过我唱歌的人才能来住。

▲
生态厕所
我还实现了另外一个建筑愿望,做生态厕所。
以前农村山水很美好,进了厕所就想逃。我要造一个厕所,打扮得很漂亮,可以坐在那喝咖啡的。这个茅草亭一颗钉子都不要,用竹皮来绑,打茅草做草甸,砍芦苇做篱笆。
干湿分离,黑水净化后才排出去。不用洗涤剂,洗碗用米糠,洗澡用手工皂,要保证我的水流到地里,植物和小动物都不会害怕。

▲
厕所里的手绘地砖

▲
屋内处处是手工的痕迹与巧思
造房子的过程,我找了表弟和一个朋友,两个帮手一起弄了差不多5个月,没花什么钱。人不应该只靠那一个东西,钱,因为那个是你要花生命来换的那一点点。


▲
村里小朋友送给岜農的春联和画
两蔸花期待像人一样/有个可以思想的脑瓜/正因为/这个脑瓜/春天过了还在思考呀
该不该开花/可不可以开花/能不能开花/应不应该开花/要不要开花
我妈告诉我当地都不种老品种水稻了。我觉得它们要是消失了,挺可惜的,就去村里收农民的老种子,然后用更健康更科学的自然农法,不打农药化肥,不用除草剂,不让土地贫瘠。
老种子的生命力强,但产量相对低。自然杂交的老种子亩产8、900斤,新品种能有1300斤,但新种子不能留种。

我现在保种了30多个老品种。每年会大规模种2-3种水稻,再小规模地种好多种,有红米、紫米、糯米,还有绿色的米。如果只是把它们存在种子库里,时间一长,它的活性跟不上气候。比如去年到今年一直干旱,它就要适应这种变化。
夏天的时候,水稻长了两个月了,因为秧苗还嫩,会被福寿螺吃。我用控水的方式,但周围的农民会打很多药。结果青蛙都凑到我这里来了,有时候吵得我睡不着。只听到我的田里“呱呱呱”地叫,其他的田怎么都静悄悄那个样子。

▲
4月末,岜農在为插秧做准备
冬天是休耕的时候,我随手一播一些绿肥和小麦种子。小麦就是种了让鸟来吃的,它们吃小麦就不怎么来破坏我播到田里的稻谷种子。

▲
岜農说理想的地方就是“稻花飘香的田野”
我这样种了10年,没有说哪一年被虫子咬得颗粒无收的。有飞虫来吃稻草的时候,蜘蛛就去抓它们。蜘蛛太多了,青蛙会跳上来吃一下蜘蛛。米太多了,老鼠会来,老鼠来了蛇又来。它们会做藏猫猫游戏在田里。
我还种了四五十棵果树。葡萄、百香果、杨梅、香蕉、黄皮果、橙子、枇杷、梨、石榴、李子、桃子、柿子、板栗、红枣……
为了榨油,种了山茶树;为了做肥皂,种了无患子树;为了做家具,种了杉木;为了做乐器,种了竹子和葫芦。山上还有随便捡的野葡萄、野杨梅、野柠檬。

▲
爬上枇杷树,吃得满手汁水
等这些树长大了就不用管了。我回来10年,再过5年,我就可以坐享其成,你知道吗?按照植物成功学来说,人工嫁接的果树,三年就能挂果,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,丰产六七年,树便衰退了。但我的老种子板栗树,不剪枝,一棵成年大板栗树一年产上百斤,它可以活100年,我都活不了那么长。


▲
乐队成员十八、路民来帮岜農插秧
他们都没在家了/有的去东莞起房子/有的去深圳学厨师/有的去福建做鞋子……
梦想总是在另一个地方/即使每年回家的时候/赚到的钱/刚够买一张/回家的火车票
--《Rongh rib》
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弹吉他,唱别人的流行歌。齐秦说他在大约在冬季,我这没有冬季,我也没跟谁约在冬季,可能我在夏季。
我在广西念的大学,念了半年就跑了。在学校里,我没有学会唱歌和跳舞,唱歌和跳舞只是个比喻,我们的精神生活不会像原来那样了,不知道毕业后该干嘛。我到广州上班,偶尔写点歌。刚出社会比较郁闷低沉,不得志,唱那些歌更加放大了我的这种困扰。
终于有一天,我听到原生态的山歌手唱歌,让我想念小时候在田里放牛的状态,很奔放,很自由,很开心。

瓦依那乐队这个名字,取的时候我在想象自己最喜欢的场景是什么。它在壮语里是稻花飘香的田野的意思。
瓦依那乐队本来只是个巧合。2006年广州有个电台的音乐节目,说要帮我做个专场演出。我就找了我的老乡索力做鼓手,吉他手李广一起排练。其实不怎么算乐队,我们就是一起演出,演完又散了,演出没什么收入,平时就各做各的工作。
2012年,我准备回老家,我想我可能不会走唱歌这条路了,那就把2006年开始的所有创作都录下来。再不整理的话,以后我的声音都变了,就更加没机会了。最开始我买不起录音设备,只能在城里上班继续挣点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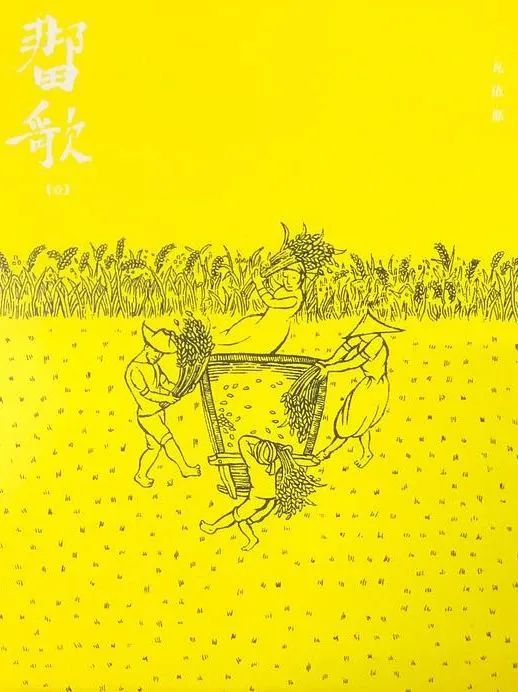


▲
那歌三部曲,封面是岜農画的
零零碎碎花了三年时间,我在老家的仓库里,在一袋袋米中间,制作出“那歌三部曲”,代表我人生不同阶段的状态。第一张《飘云天空》是去外面流浪,去山外学习。第二张《西部老爸》是去了广州回来,重新去看家乡。《阿妹想做城里人》是在思考我到底该在哪里生活。
做完专辑后,我们没有宣传。巡演走了一圈,底下只有几个喝酒来的人。我觉得我好像在做罗马柱哦。也没想太多,那就继续去生活,出发回家了。

▲
自己种竹子,造自然乐器
在老家的这些年,瓦依那没再发过一首歌,但我并没有放弃音乐。我去找壮族的传统乐器,好多都摆在博物馆里,没什么人弹奏了。我用树叶、竹子、葫芦、酒坛、打谷桶做自然乐器,去采风收集快消失的民谣。
前几天坐火车,安检的小姑娘说锄头不能通过。为了证明它是安全的乐器的身份,我唱了两句种田歌给她听。她看了我的票,终点站的确是回家种地的。于是锄头安全过关了。她还问我有没有走地鸡卖,我说我卖有机大米。

▲
岜農发明的乐器“赛德”
我现在在乎的只是,这个声音,是不是熟悉的这块土地发出的。
鼓要有很大的回声感,因为广西喀斯特地貌,不管钻进哪个山洞里,都是呜呜呜,咚咚咚,嘣嘣嘣。葫芦琴是我们广西的特色,共振板用竹子的竹衣来做,竹壳很薄,声音很亮。水竹琴传统只有两根弦,用小棍子敲节奏,我多做了几根弦,弹拨出旋律。弹的姿势刚好要把它放在肚脐那里,我就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赛德,壮语里脐带的意思,它是可以跟天连在一块的通道。

▲
在米袋上画画
晚上我坐在回廊上打鼓,风吹起稻浪,青蛙是主唱,我就帮它伴奏,我们融在一起。我会成为一股风来唱歌,会变成一只鸟来唱歌。

今天又来唱山歌/阿哥阿妹一起来/山上月亮亮汪汪/照见阿妹像朵花
阿哥就是爱阿妹/我俩就在山里住/阿妹也说爱阿哥/就是想做城里人
--《阿妹想做城里人》

▲
挑担游峒溪,歌飨有缘人
两年前,桂林的一个农民十八来帮我收割,他平时会在街边唱歌。再加上在工地做砌墙工的路民,重新组成了瓦依那乐队。去年疫情时,感觉大家都很压抑,我想我要发出农民的声音,为什么不能用握手的方式去跟万物连在一起?
于是就做了“岜農大米,世界一体”的巡演。我们广西山歌手,天不怕地不怕,心想唱歌就唱歌,欢迎表妹和表哥。不过刚巡出广西,到广东就阳了回来了。


▲
在山林,在舞台
图源声音共和
跟我唱歌的大人叫瓦依那,跟我唱歌的小孩就叫土人合唱团。村子里很多小孩子是留守儿童着,跟爷爷奶奶在家。有一个我来带他们唱歌,他们都好开心。

▲
土人合唱团
我教他们唱壮语歌,为他们写童谣。看到孩子们背着比自己还重的书包去上学,就写了一首《美丽山坡》,讲的是麻雀妈妈不会告诉它长大后要成为一只有意义的麻雀,但它还是成为一只很好的鸟。雨水的妈妈不会教育它要成为什么雨,但它也会滋润土地。睫毛妈妈不会告诉它长大要成为一双怎么样的睫毛,它天生就会挡着汗水。花朵的妈妈不会整天在教育它,但它也一样会开得很美给这个世界。
森林里的动物,没有这些教育,就会带来美好。我在想教育有时候给生命赋予作用,会变成过度的欲望。希望小朋友有不被束缚的生命力,还记得土地是养我们的,我们应该去爱它。
因为唱歌也没有太固定的演出收入,这些团体都很松散。如果你喜欢我,我也喜欢你,我们就在一起唱。


▲
野趣
其实回来挺难的。乡下有一种封闭的力,外边又是太开放的力,而大的氛围依然红尘滚滚。之前帮我修房子的表弟,待了几个月,就说我还是回流水线上班,这里太冷清了,没有KTV和烧烤,连一个姑娘都没有。
山里的确是很冷清的,如果你把握不好自己的节奏,你会觉得孤独。我现在单身,村里经常介绍对象去相亲,送了好多只鸡好多只鸭了。正好有一个矛盾,想要淳朴(的姑娘)了,好像跟我的思想又有点远,思想能开阔一点的话,她又不想在乡下待着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是个隐士。我的确离开了人群,离开了漂亮的姑娘。但是,这里存在以退为进。原本在城里,满街都是设计师,没有一个机遇的话,我做什么都做不好。回来以后,我很笃定,只要有一口饭吃,我可以不为别人做,空下时间来专注做我内心里理解和喜欢的事情,反而能做得更出色。也是回来以后才发现,诗与歌的种子,早早就种在儿时的山野里,花鸟虫草,阿公的神奇故事、阿妈的歌谣都一直在照耀、滋养种子生长。

▲
夜色温柔,写诗、饮酒、入睡
好多人说我们再也回不去故乡了。我有点不喜欢这句话。我在想,你去外边玩了,突然想回故乡就回故乡,谁帮你守住故乡?
我手上有老茧,自己来建造。
我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。如果有一天,连这里都不可能做我想要的事,那只能做我内心里的小小的院子,种我内心里的那块田。
他辞职回广西:低头种地,抬头唱歌 | 文学
摘要:
八年前,一个叫“瓦依那”的广西壮族乐队,
在自家仓库里录制了三张专辑,
随后销声匿迹,踪影难寻。
有乐评人称“那歌三部曲”是沧海






